王缉思_中美间和平能够基本保障但要警惕擦枪走火的可能性_新春观察
虎年新春之际,直新闻推出特别策划《新春观察》,约访多位知名国际关系学者,与您共度知识年。在百年变局与世界疫情相互叠加,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当下,我们将迎来一个怎样的新年?又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新一年呢?《新春观察》第一期,带来的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的专访。专访由直新闻驻京记者站记者唐萍采写。

【记者手记】
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任后就说过,美中关系无疑是未来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。也有美媒说,中美关系可能是人类史上最危险的双边关系。2022年,中美关系究竟将何去何从?
国内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有很多,王缉思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。从1982年在牛津访学期间的一篇论文开始,王缉思与中美关系研究结缘40年,一路的研究历程伴随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。王缉思曾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,现在仍在北大任教,并长期兼任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,有媒体将他称为“钻进白宫心脏的中国行者”,以此来形容他对美国问题的研究深度。
在访谈前,王老师一直说自己很紧张,还问能不能就聊天,不做采访。访谈当天,我们提前布置好机位等待王老师。不多时,一个黑色的身影推门而入,王老师穿着一件北大校服羽绒服,背着双肩包,独自来了。一进门,王老师边脱掉毛衫、换上西服,边跟我寒暄。王老师主动“采访”我,问我的教育和工作背景,他解释说,“我要先了解你这个人”。我们的访谈从了解人开始,访谈后,王老师告诉我,人与人的、面对面的交流,对中美关系也是极为重要的。
王老师谈得很放松,越谈笑声越多。对这个他研究了大半辈子的领域,思考与洞察就在谈笑间自然地流淌出来。谈起中美关系、美国政治、国际形势,王老师无不是深入浅出,在访谈录制结束后,我们又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个多小时。王老师告诉我,他去了70多个国家,这对他研究美国也是有帮助的,美国的政策影响世界,去了解当地人怎么看美国,丰富了他对美国政治的理解。我也说起我的留学经历,出国后,自然而然地就会拿外国与中国来对比,差异、碰撞、思考、理解、包容就这样“随风潜入夜”的萌发。“我们还是要多出去看看,多交流”,王老师说,他跟美国的学界、政界人士私下交流,大家都为中美的人文领域交往降温感到遗憾。王老师向我透露,3月份他将飞去美国,调研当前美国政治形势。我问王老师,“您知道您被媒体称为‘钻进白宫心脏的中国行者’吗”,王老师听罢笑了说,“白宫是去过,但有没有钻进心脏,我就不能说。”
这无疑是一次如沐春风的访谈,当晚,我们都给彼此发了一句话——You made my day!
在整理访谈录音时,我摘录一些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观点:
· 和平能够基本上得到保障,但是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有的。比如说南海的问题,更可能是台湾问题,两个国家军队现在已经挨得很近了。
· 一个世界性的现象,就是政府的权威不够,特别是在所谓的民主国家,西方国家政府的权威现在是越来越下降了。
· 现在已经可以说,世界的权力相当分散,而且继续会分散下去,我不大喜欢用多极化的说法,我说更多是一种分散化,就是多中心。
· 2022年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是还没有过去的新冠疫情风险,但是世界经济总体来说,没有往上走,跟疫情发生之前的世界经济已经有很大的变化。经济也好,贸易也好,发展的速度没有过去那么高了,也就是低速的发展,恢复到疫情之前,是一个很长的过程,需要几年的时间。在这个过程中间,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财富分配的问题,这是我觉得一个关键问题。
·除了新冠疫情以外,社会不公平不公正,财富分配仍然倾向于富人的这个现象可能很难改变,也就是说,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动荡不安,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,特别是一些本来发展就很不平衡的国家,就会发生内乱。
· 中美两个国家最好的情况,在2022年就是说相对平稳,没有大的碰撞,没有大的挫折,这就是最好的结果。
中美关系还会好吗?这个问题要时间给出答案,但希望中美关系好的人,或许比我们想的更多。

【专访实录】
唐萍:首先想请您分享一下,您是怎么走上研究中美关系这条道路的?
王缉思:我从硕士生时候开始研究国际关系,但是我的导师说你的水平太差了,你的基础太差了,你别研究大国了,研究一些第三世界。后来我就跟我导师商量,变成研究东南亚。因为我到牛津大学进修的时候,牛津大学那边没有什么东南亚的专家,所以我的导师就给我布置一个题目,最后一个题目写的是40年代后期的中美关系。他的问题是,当时美国为什么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打内战,而反对共产党?他说是不是因为如果共产党掌权了,那么苏联可能跟中国结成同盟,对美国在冷战中间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。他说你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,后来我就去做了这么一个题目,做完了以后在牛津还发表了一个演讲,导师很满意。我回国以后,我在中国的导师,薛谋洪老师就跟我说,你赶紧交一篇硕士论文,我本来是想写东南亚的,结果急急忙忙之中,就把这篇论文变成我的硕士论文发表了,也没有发表,就是说通过了。通过以后开始收不住,就开始研究中美关系,然后逐渐就走上这条路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觉得我还是有点潜力的,就把我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,那时候叫国际政治系,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,先当副所长,后来当所长,一干干了十几年,所以就这么样一个过程。
唐萍:您去牛津访学那一年就是1982年,到今年正好40年了。中美关系40年里面有很多风风雨雨,您有什么感受?
王缉思:这个感受就是,中美关系其实有些规律性的东西,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?我的研究结果是觉得,这是由两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决定,这是最主要的,当然也有国际氛围的一个大环境。比如说在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,和冷战结束之后的中美关系有点不一样。但是中国的国体、政体决定了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,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,它有它的价值观,跟中国价值观不一样,它又想保持它的世界地位,也就是说两个国家的国内政治、传统的文化价值观,有很多的不同,当然也有一些共同利益,这样就决定了双边关系是这样。它其实不是简单由人为决定,不是领导人换届等等决定,它是几个不同方向的,或者说几个不同的因素决定的。
比如说,一个因素是两个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。我刚刚研究中美关系,1982年或者是更早的时候,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也许十分之一都不到,现在已经到了美国的百分之七十多。那么当然,实力对比的变化就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影响。然后中国更往前走的时候,就是毛泽东时代,中国的国内政治跟美国的国内政治差别非常大,两个国家互相是没有往来的。有了往来之后,两个国家实际上是产生了一些互动,这互动就说中国觉得美国的某些地方,包括它的市场经济是可取的,然后美国又觉得中国在大的战略利益方面,跟美国有共同利益,就走到一起来了。但是逐渐走着走着,这些事情又发生了一些分化,所以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国内政治、国际环境、国家之间力量对比,这几个方面互动的结果就产生了现在的中美关系。

唐萍:建构主义那种感觉。您最近发了一篇文章,我看到朋友圈好多学者在转,可以请您谈一谈什么是中美关系中的“热和平”范式吗?
王缉思:我在2001年写了一篇英文文章,就讲到中美关系不是“新冷战”,实际上是一个“热和平”。当时我说“热和平”的时候,想的是两个热,一个是吵架吵得很热,其实在2001年就已经产生了人权问题,一些国内政治问题,比如说美国对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不满意,都已经产生出来了。其实1999年炸馆事件,也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很强烈的影响。2001年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,已经发生了中国和美国的军用飞机在南海附近上空相撞的事情,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这个是热起来了,热起来就包括是有可能打仗的,吵架吵得很凶。
另外一个热,在当时就是(中美)经贸关系开始热起来了,中国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,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,以每年双边贸易增长10%的速度往前发展,这也是热起来了。然后再加上,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是一个热潮。在2001年前后,这些都是热的,所以我说这是一个“热和平”,不是“冷战”。
但是今天再回过头去想,这个吵架还是接着在吵,而且有些地方比过去还热,比如说南海的问题、台湾的问题,在当时没有现在这么热。还有两个国家,关于哪个国家更民主,我们说是我们是全过程人民民主,美国说它才是真正的民主,这个也吵得不亦乐乎。吵架比过去吵得更凶了,包括新冠疫情溯源的问题,还有冬奥会的问题,好多问题都吵得很热,但是经贸反倒冷下来了,这个热就跟当时的热有点不一样,就变成只是吵架的热,而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冷下来了,这仍然是一种热,可是这种热不是当时的热,当时热比现在热要好,或者说当时热有两面,现在热变成一面,这使我感到有些失落。

唐萍:但是我看进出口数据,去年中美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还是很大的,对吗?
王缉思:如果说经贸关系本身的话,双边的贸易额还是在上升的,这点还是令人比较感到鼓舞的。但是未来是不是这个样子很难说,因为现在新冠疫情的结果,可能西方某些国家恢复得比较快,而中国对新冠的警惕性比较高,所以我们国内的各种各样的防御措施,可能比西方要更为严格一些。
如果是这样的话,西方国家还有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,它们逐渐地经济恢复起来以后,对中国的制成品的需求可能会下降。这样的话,经贸关系也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。但是,我对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还是比较有信心的,实际上你不可能完全“脱钩”的。但是让我更感觉到有某种不安的情绪,是技术“脱钩”。美国对中国采取技术“脱钩”、技术封锁的方式。
唐萍:尤其是高技术。
王缉思:对,就是说所谓的技术“脱钩”、技术封锁。比如说打击华为,打击中国的一些通信技术产业。这些可能使两国产生更大的矛盾,或者是我们本来希望从美国得到的技术得不到,然后我们想派更多的学生到美国去留学,这个可能也是相当困难。
唐萍:但是您这个“热”,后面还是跟着“和平”,用“和平”来框住,是不是还是有一种“斗而不破”的意思?
王缉思:对,我认为和平能够基本上得到保障,是因为两个国家在元首通话的时候也多次讲了,我们不希望发生“新冷战”,不希望发生政治战争,就说明更不希望发生一些热战。中国跟美国不是没打过热战,朝鲜战争的时候,大家看长津湖不是打过热战吗?但是谁会希望中美之间发生另外一场战争?两个国家我相信没有人会愿意发生这样一场战争。
但是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有的。比如说南海的问题,更可能是台湾问题,两个国家军队现在已经挨得很近了,飞机军舰等等,但是如果发生擦枪走火,就有可能爆发成更大的战争。不过我觉得双方的军事领导人,一直到具体的军事部门,他们都是管得很严的,不能让突发事件变成两个国家之间大规模的战争。
所以我觉得,首先是两个国家的元首、政府部门都不希望打仗,老百姓也不希望打仗。如果不希望打仗,那么万一出现擦枪走火的情况,就要把它控制下来。所以我觉得和平是有保障的,我不觉得两个国家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,只是说,什么事情你都需要发挥想象力,三年以前,没有人想象有新冠疫情出现,如果三年以后,中美之间真正发生战争,你也没办法。某些事情使人失去某种理智了,你就打起来了。如果正常情况,那就是不打仗,可是这个矛盾避免不了,所以就发生一个不断的碰撞,但是又不打仗的局面。
唐萍:现在还是有危机管控。
王缉思:对,双方都有危机管控的机制。当然不是很完善,我们作为研究的人也不觉得很满意。但是,实际上双方还是有沟通的,包括从最高领导层,一直到军事部门、外交部门等等都有沟通。

唐萍:再问一下美国内政的问题,今年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,您对选举形势有何研判?
王缉思:现在来看,多数人在预测说民主党会惨败,他们算得很细了,每个州、每个选区、还有选区会发生某些变化,共和党从气势上来说现在在上升,民主党可能至少失去两院中的一个,甚至两院都失去也是可能的。但是就像过去我们预测美国的政治一样,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,去年这个时候,2021年初,2020年年终的时候,有多少人说我敢肯定是拜登当选,或者我肯定是特朗普当选?说了也没什么意义,因为直到最后一分钟才确定。
所以我也不是非常肯定民主党一定输,只是现在觉得大概率是它要输。不过又有一个信心,输了以后并不说明民主党从此以后一蹶不振了。美国政治一贯是这样,中期选举变了,然后再过两年选举又变了,如果过两年选举,共和党回来了,再过四年可能民主党又回来了。美国一直是这样的,政治上左右摇摆,然后两党之间争权夺利,这样一种大的局面没什么变化。
唐萍:其实您刚才也说了,还是很多人不看好民主党中期选举形势,跟拜登这一年的执政表现有什么关系吗?
王缉思:首先,拜登第一个败笔就是阿富汗这件事情。拜登大概也没有想到,不只拜登没想到,当地的塔利班自己都没有想到,那么快就取得政权,更不用说,巴基斯坦政府、阿富汗当时的政府也没有想到,其他国家恐怕也没有做思想准备。但不管怎么说,它输了,一下子塔利班就回来了,美国就撤走了,这对它是一个大的打击,再加上美国的经济,虽然从表面上来看,好像还在增长,就业也在增长,但是老百姓没有感觉到经济增长对他们的生活有多么大的推动,或者说,经济的数字并不能说明他们的生活改善了。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。美国的股市好像还可以,经济的数字也还可以,但是普通的百姓没有从这得到很多的好处,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处理也不是那么好,所以普通民众不满意。
而且美国留下了历史上一个烂摊子,它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,共和党也在煽动,包括一些白人的种族主义。民主党认为它代表穷人的利益,代表少数族群和妇女,或者是同性恋等等少数、弱势群体的利益。共产党也在炒作,他们才是弱势群体,觉得拜登这些有点做得过头了,所以觉得拜登的内政有点太左了,或者说他偏向所谓少数的族群了。
唐萍:可是有些人还嫌他不够左。
王缉思:美国有一个一贯的情况,你要问美国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,大部分人总是说,“不是”,没走正确。现在如果问的话,还是这个样子。特朗普上了以后也是,问美国是否走在正确道路,大部分人也说不是,这也是一种常态,就是老百姓不满意,对政府不满是一个常态,这几年尤其不满意,这就不是常态了,这有一个世界性的问题。
我说的身份政治的问题,就是说他自己处在一个什么立场上,他自己的感觉是什么,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投票。但是这些东西并不一定可以从客观的角度去理性分析,他就觉得,我就支持那个。我觉得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,就是说政府的权威不够,特别是在所谓的民主国家,西方国家政府的权威现在是越来越下降了。

唐萍:您刚刚也说有的人是嫌民主党太左了,但是现在也有人嫌拜登还不够左,民主党内还嫌他不够左。以前是两党的分裂,现在感觉民主党党内都有点分裂了?
王缉思:民主党一贯有一个问题,就是它自己很难有一个凝聚力。共和党的凝聚能力比较强,因为首先从种族的角度来说,白人富人居多数,它打出的旗帜是,“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”,或者“美国第一”,这些东西都打动人心。民主党,说得难听一点,乌合之众。你怎么把不同的人搁在一起呢?这些人都搁在一起,他有他的难处,他也有他的难处,但你把这几个不同的人群搁在一起,就没有凝聚力了。
如果你说“黑人的命也是命”,那白人怎么想?或者妇女说我支持黑人,或者同性恋说支持黑人。黑人只是民主党支持者中间的一部分,而这一部分现在也发生了分化。因为有人觉得,他没有从民主党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。比如说奥巴马的8年,是一个黑人当了美国总统,但是黑人在这8年里,并没有感到自己的处境得到多大改善,所以连奥巴马的黑人总统他都不支持的话,他怎么会支持现在的拜登总统?所以民主党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危机,它的凝聚力在下降。
唐萍:但是很讽刺的是,民主党的口号也是“unite America again”。
王缉思:对啊,两党都需要打出一个,好像我可以把美国人带到一个更高的水平,或者美国的国力得到提升。实际上两党都做不到这一点,那么普通民众就会感觉到失望。我对美国政治的观察,觉得美国现在确确实实,从软实力来说,从它国家的凝聚力来说,都是在下降的一个过程中。

唐萍:还有一个您文章里也提到了,2022年中美都有一些迫切的国内议题,随着中美两国都把重心转向国内,会不会导致全球领导力的一个收缩?
王缉思:这两个国家在世界上确实都有很强的影响。美国有它这一帮的伙伴,西方国家。不管怎么说,西方很多欧洲国家,甚至韩国、日本对美国也不服气,但是跟美国比起来,它们还是相对弱一些,所以美国还是一个带头的。所谓这种影响,这种领导力,它是有限的。中国国力在发展,在发展中国家确实也有很多号召力,但是从整体来说,是不是能够说,中国的号召力就达到了某种程度,或者跟美国平起平坐,也还没有。
所以两个国家都集中在做自己国内问题,跟前几年比,我没觉得有太大的变化。就是说,其实前两年,两个国家也都在集中自己国内问题,不是想在世界打仗。问题是,现在的一些世界性问题,必须把这两个国家拉进去,比如疫苗的问题,气候变化,还有经贸的关系,WTO等等这些问题,都离不开两个国家所发挥的作用。
所以,想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国内也是不可能的,它还是要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国际事务上。所以,我没觉得有一个领导力普遍下降的问题。现在已经可以说,世界的权力相当分散,而且继续会分散下去,我不大喜欢用多极化的说法,我说更多是一种分散化,就是多中心。
唐萍:这几年中西方的博弈中,我们频频看到两个关键词就是“主权”和“人权”,中国可能谈主权比较多,西方谈人权比较多,您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?
王缉思:中国当然主张主权高于人权,从中国历史上、文化上就是这样的。国家总是比个人要高,你看大街上的口号,“人民有信仰,国家有力量,民族有希望”,那谁有力量呢?没有反过来说,人民有力量,国家有信仰,不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从这些普通的、我们正常看问题的方式,你就知道中国一直是从社会到个体,都认为国家或者集体要高于个人。
但是美国不是这样看的,它没有这样的一种口号,它说“让美国再次强大”起来,其实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个人,就是你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比过去更好了。美国的传统文化,它的基督教文化,基督新教的文化就是提倡个人的权利。比如说,美国独立宣言第一句话就是,我们翻译成“人人生而平等”,实际上更精确的意思是,“人是被造为平等的”。怎么被造为平等?被谁造为平等?上帝造成,造物主造成的平等。
就是说,在美国人眼里,上帝是第一位的,神是第一位的,下边就是个人了。个人可以通过自己读圣经、到教堂,就跟上帝直接沟通了,有一个中间环节,那就是国家。所以你要告诉美国人说,这个国家的权力应该大于个人的权利,政府的权力应该大于你的权利,他不能接受。而且不光是美国,整个西方,特别是从文艺复兴开始,就提倡人权,说个人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等等这些东西。
这是西方文化中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东西,它认为人权是要高于国家的权力的,政府对社会的干预是有限的,这些东西也是西方现在深入人心的。所以普遍来说,西方人可以接受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。就是说,实际上主权是代表一个人权,是这么一种观念,这样的话,中西之间确实有很多的差别。
不过,你要说国家是不是要对个人生活产生影响,通过新冠疫情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了,如果国家不发挥作用,新冠疫情在西方国家没法控制,所以它要求你要戴口罩。有些西方人就说,我就不戴口罩,你凭什么要让我戴口罩?你政府管得了别的,你可以管社会,你管我个人戴不戴口罩,我就不戴。你要强迫我戴,我要上街游行。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,叫你戴口罩是为了你好。
唐萍:但是他就是说,我不是小孩子,不需要你为了我好。
王缉思:对啊,我们对小孩也说,我是为了你好,那你当然要服从我了。所以这就是两种不同文化,这并不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,它会产生一个文化问题,产生一个人的观念问题,要把这个想通了,其实很多国际上的事也就没有那么严重了。
唐萍:就没有那种硬杠了。
王缉思:你很难去跟人西方人说,主权比人权更高,就sovereign rights are higher than human rights. Individual rights are subordinated to states rights。而且你说的sovereign rights,实际上是指的主权国家。而在国家这个层面,它也有不同的层次,有一种就是说,国家就是政府代表的,政府的权力和整个国家sovereign rights也是不一样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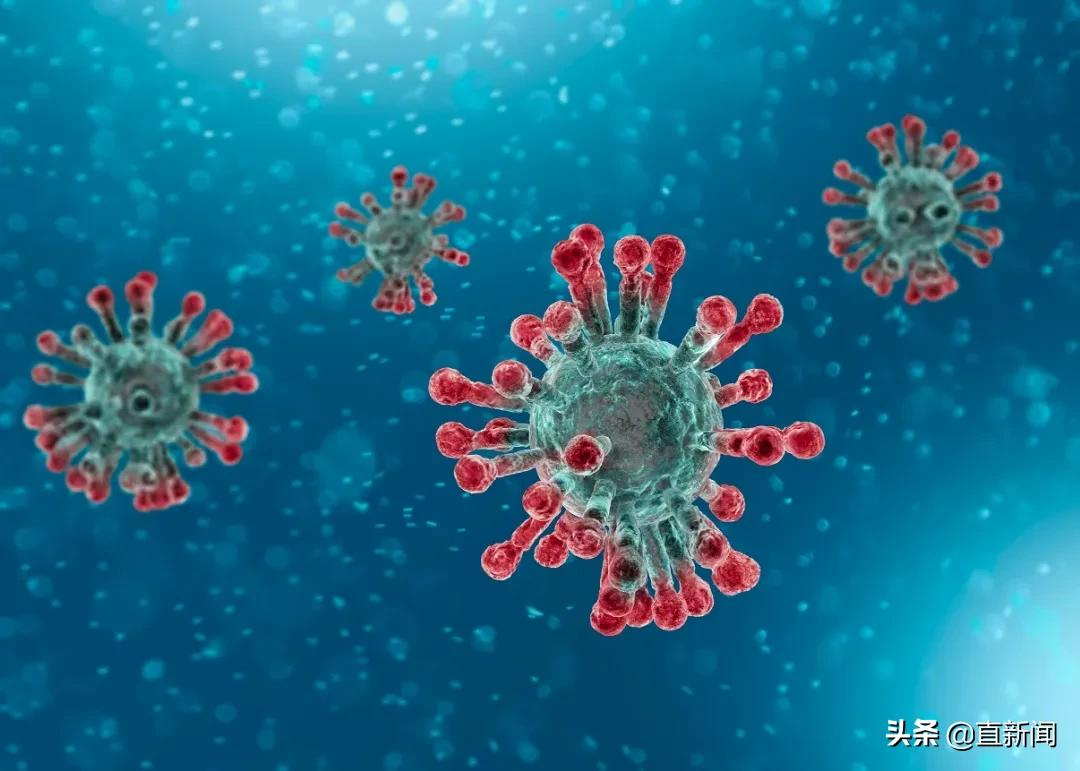
唐萍: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,给整个国际格局带来了深刻的影响,您有何观察?您觉得2022年有哪些风险值得我们警惕?
王缉思:2022年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是还没有过去的新冠疫情风险,但是世界经济总体来说,没有往上走,跟疫情发生之前的世界经济已经有很大的变化。经济也好,贸易也好,发展的速度没有过去那么高了,也就是低速的发展,恢复到疫情之前,是一个很长的过程,需要几年的时间。在这个过程中间,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财富分配的问题,这是我觉得一个关键问题。除了新冠疫情以外,社会不公平不公正,财富分配仍然倾向于富人的这个现象可能很难改变,也就是说,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动荡不安,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,特别是一些本来发展就很不平衡的国家,就会发生内乱。
国际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,比如说美国跟俄罗斯,或者是中国跟日本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,但是内部的动乱可能产生一些外部的波动,国家之间受到这种影响。如果说得更深一点,内部收益分配不平衡,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来扭转呢?这是非常难的,也就是说共同富裕,大家都可以接受,都希望共同富裕,但是在人类历史上,在美国国家历史上,共同富裕的例子并不多。你说哪个国家现在实现了共同富裕?不但没有实现共同富裕,而且几乎所有的国家,收入分配差距都在扩大。原来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,比如说丹麦、日本、北欧、瑞士等等,也开始发生了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,这样的话对世界是不好的,这个是很难克服的。就是说财富增长还是很容易的,总体财富增长很容易,但是你要使财富比较公平去分配,这个很困难。而且什么叫公平?难道大家都分一样的钱就公平吗?有人说我挣得多,为什么给我分得少?我比人干得好、干得多、我创造价值大,然后给我分的跟创造价值小的一样多,当然我不干了。也就是说,他也感觉到不平衡。
可是你看现在这个样子,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到现在,全世界的富人的财富还在成倍增长,说明什么问题呢?按理说世界经济在下滑,这些人(的收入)是不是也应该下滑,没有,股票还是在往上走。问题在哪呢?这不是我政治学家能够解决的问题,主要是经济学家应该去解释,或者去想办法克服这个东西,但是很难。比如说,你给富人加税,很多国家的政府,包括美国政府在内,是富人的政府,你给这些人加税,让他把钱拿出来给普通人,他不干了,而且他也觉得不合理,为什么我创造了这么多财富,我要把钱给他,我自愿地给他可以,我弄个扶贫项目,但是你通过税收的方式,你还要怎么样?我交的税已经够多了。在穷人看来不是这么回事。
唐萍:最后一个问题,您对2022年的中美关系乐观吗?
王缉思:不乐观也不悲观。2021年的中美关系相对来说是平稳的,比2020年、2019年、2018年时候的直线下滑有所缓和,就是比较平。2022年,我觉得可能这样一个比较平的方式还会继续下去。
几个原因,一个是中美都集中在国内的议程上,中国要开二十大,美国要中期选举。两个国家都要对付国内的疫情,还有经济的发展等等。但是要改善也是很困难的。原因是美国国内政治,我刚才讲了,美国在四分五裂的过程中,有人觉得需要寻找一个外部敌人,中国在筹备二十大的过程中,你要让中国对美国作出重大的让步,觉得我们哪个地方做得不对,做得不好,这也不可能的。我们只有更进一步加强对美国的警惕,比如美国想搞“颜色革命”什么,我们是很有看法的。所以,在这个情况下,在台湾问题上,其他的问题上,都不会作出让步。所以两个国家最好的情况,在2022年就是说相对平稳,没有大的碰撞,没有大的挫折,这就是最好的结果。
记者 | 唐萍,深圳卫视驻京记者
编辑 | 曾子瑾,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
专题统筹 | 曾子瑾,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